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2017年入冬以来,各地相继进入流感季节性高峰,流感样病例就诊百分比和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均显著高于既往三年同期水平,重症病例也比往年明显增多,各地医疗机构诊疗压力增大。
其中,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在朋友圈持续“刷屏”,一场流感,牵动一家人,也牵动了大半个中国。2017-2018年冬季的这场流感疫情,深深地镌刻在众多医护人员和他们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属的心里,有胜利的喜悦,更有生命难以挽救的惋惜和悲痛。
伴随着一场小雪,北京的流感形势也逐渐回落,但是,当我们回顾刚刚经历过的4个月,不禁去追问:究竟这场流感有何特点呢?关于重症流感救治,从事呼吸危重症的一线医务人员有何经验、体会?如何降低重症流感的病死率?社会众“声”相究竟如何,带给我们哪些思考与启示?为了更好地诠释上述问题和汲取经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重症学组组长解立新教授特别策划了“重症流感专题”(05~06版),敬请关注!
2017-2018年冬季北方地区流感特点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解立新

在黄河以北、尤其是在北京地区从事呼吸危重症的医务人员,会对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的流感肆虐记忆犹新,很多医务人员春节期间可能是在救治重症流感患者的一线中度过。当回顾刚刚过去的流感,我们又想起了2003年的SARS和2009年的流感。那2017-2018年冬季流感又有什么特点呢?
2018年3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布的北方地区流感病毒监测报告指出,2017-2018北方地区主要流行的流感病毒为A型H1N1亚型流感和B型Yamagata亚型流感病毒,A型H3N2亚型和B型Victoria亚型流感以低水平共同流行,其中重症患者多感染H1N1流感,老年患者中也有H3N2亚型流感重症病例。
流感病毒有两个最主要的表面抗原: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是中和抗体的主要靶点,均有多种亚型,它们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组合,就产生了上百种的流感病毒亚型,但其中具有较高传染性的亚型并不多。比较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常在人群中流行的H1N1和H3N2(均属于甲型),和常在家禽(多指鸡、鸭等)中流行的H5N1和H7N9。国家卫生计生委和CDC在2013年将A型流感(H1N1和H3N2)和B型流感一起作为季节性流感(流行性感冒),纳入国家法定传染病的丙类,禽流感H7N9作为乙类传染病。
流感病毒变异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抗原漂移和抗原转变。抗原漂移可以使感染过的宿主再次感染。而抗原转变可以产生新的亚型,往往使不同宿主、甚至是不同种的宿主所感染的流感病毒遗传物质重配,有些甚至可以跨越物种屏障传染给人类,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在猪之间、鸡鸭之间传播的猪流感、禽流感让人们陷入了空前的恐慌。
根据我国的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特点,从时间分布上看,南方的流感高峰一般集中在3~6月份,北方流感高峰集中在12月至来年1月份。
根据北京CDC发布的流感样病例监测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市流感的流行一般集中在11月初至来年1月;根据北京市2015-2018年流感样病例,可以看到2017年11月初到2018年1月初出现了一个中度较高水平的流行。
2017-2018年这个无雪的冬季,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会永远深深地镌刻在众多医护人员和他们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属的心里,有胜利的喜悦,更有生命难以挽救的惋惜和悲痛。在救治重症流感的日日夜夜,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生命的宝贵和医学的不断进步,体外膜氧合(ECMO)的有效应用为我们救治重症呼吸衰竭提供了重要的利器,明晰了重症感染与免疫失衡的根本关系,指引着我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整好行装,继续前行。
2017-2018冬季重症流感诊治回顾
中日医院呼吸中心 熊舒煜 詹庆元

詹庆元教授
在2017-2018年的流感季节,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部/五部共收治55例重症流感患者,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于外院转诊。甲型流感占7成,以H1N1为主;乙型流感占3成。与往年相比,本次流感疫情更为凶猛,患者呈现年纪轻,病情重,合并感染多的特点。
自2017年12月11日起,本中心收治的重症流感患者,年纪最小的仅15岁,最大的87岁,平均年龄54.4岁,其中60岁以下的患者占到58%。男性比女性稍多,占到56.4%;体质指数(BMI)在24 kg/m2以上的超重或肥胖患者占6成;40%的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不到一半的患者合并糖尿病;近1个月有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用药史的患者占30%左右;极少数患者存在慢性肺部疾病。
这55例重症流感患者中,53例存在呼吸衰竭。16例需ECMO支持,这部分患者病情最为危重,尽管给予了足量足疗程的抗感染治疗,以及充分的支持治疗,病死率超过50%;28例需要有创通气,其中4例进行了气管切开,这部分患者平均年龄超过60岁,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APACHE) Ⅱ评分中位数高达20分,最终约一半的患者死亡,其中大部分合并院内感染;其余11例患者经抗病毒及无创通气或经鼻高流量氧疗后病情好转,这类患者入重症监护室(ICU)时的病情相对较轻,住ICU时间也最短,大多在1周内转出。
治疗上,对大部分患者应用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剂量可达150 mg,间隔12小时;对少数患者应用帕拉米韦,剂量为300 mg每日一次或600 mg每日一次。抗病毒治疗的时机偏晚,从发病到开始抗病毒治疗的间隔时间,中位数为8天,远超过指南建议的发病内48h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推荐。不少患者在起病之初没有得到可靠的病原学结果,按照细菌性肺炎进行经验性治疗,使得流感的确诊时间较晚,抗病毒治疗也因此延迟。起始抗病毒治疗后,流感病毒核酸转阴所需时间从2天到25天不等,中位数为9天。
合并感染方面,40%患者在入ICU之初即存在细菌、真菌或其他病毒感染,其中包括巨细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MS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以及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属等。
在流感后合并感染的各种病原体中,曲霉菌属最为突出。共16例患者临床诊断出曲霉菌感染,其中9例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培养出曲霉菌属,7例通过血与BALF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以及影像学诊断。
出乎意料的是,年龄、BMI、糖尿病病史、淋巴细胞绝对值均不是曲霉菌感染的危险因素。流感病毒对呼吸道上皮细胞的破坏,以及免疫功能的打击,使流感患者成为曲霉菌的易感人群,这在临床工作中须引起特别重视。
总之,在流感高发的秋冬季节,医务人员须加强对流感病毒感染的识别能力,从而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开展规范的呼吸支持治疗,早期给予抗病毒治疗,同时高度警惕曲霉菌属等合并感染的诊治,是降低重症流感病死率的关键。
生命可贵,难言放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孙兵 北京宣武医院 李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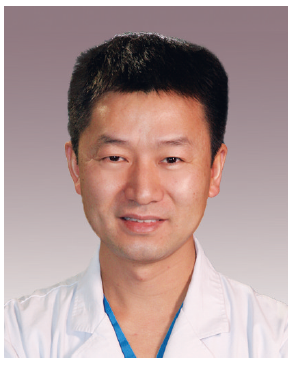
孙兵教授
从医院每天汇总的发热门诊就诊人数能大概看出,北京的流感形势在进入2018年3月份后,便逐渐回落,北京的这个流感季总算快要过去了。回看这4个多月的历程,每一个身涉其中的医护人员应该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北京过去的4个月的冬春,未见一场雪,流感趁机肆虐,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次流感似乎比以往更难治,尤其是重症病例。于己而言,确实也感同身受。回首这几个月,或忙,或累,更有同事和自己“中招”后的崩溃。但是,职责所在,使命使然,没有必要标榜神圣,更不必矫情。只是不能看淡的生生死死,贯穿始终;面对意外和无奈,即使我们这样一个呼吸重症监护室(RICU),这群从SARS、甲型流感、禽流感一路走来的“老”医生,也难以释怀。
记得元旦后收的一个37岁的四川小伙子,甲型流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发病已经2周,在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治疗5天,从无创到有创,逐渐加重,还出现了左侧气胸,氧合不能维持,转到我们RICU做体外膜氧合(ECMO)支持。我们尝试拔除气管插管、清醒ECMO并未成功,重新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放醒后,患者出现了新的右肺脓肿、脓气胸,细菌真菌混合感染,胸腔闭式引流不能复张。医护人员也曾一度崩溃、丧失信心,但未放弃。最终患者在近3周后成功撤离ECMO,并逐渐好转出院,无需家庭氧疗。回想当时患者病情最重、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如果成功说服家属不再坚持呢?
而对另一个孕妇,我们则颇感无奈。记得那天下班时接到医院通知,外院要转入一个呼吸衰竭孕妇,怀疑甲流肺炎。可等到半夜也没消息,原来患者傍晚在外院早产手术,想想手术都能做,说明病情不重啊!于是放松了。等患者被送到急诊抢救室,我们才发现患者病情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从气管插管后人工气道一次性喷出300 ml血水样液体开始后的48小时,即使给予30 cm H2O的呼气末正压(PEEP)、静脉-动脉-静脉体外膜氧合(VAV-ECMO),患者的氧合和循环仍维持不住,气道中的血水一直如泉涌,直到去世。患者去世后回报H1N1阳性、血培养葡萄球菌阳性。
一个30多岁的鲜活生命稍纵即逝。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患者直接被送到RICU会怎么样?如果提前了解一下病情会怎么样?如果……
下面这位也许是这个冬天诊治的最重的患者之一。当一位因为风湿免疫病长期口服激素与免疫抑制剂的60多岁阿姨从外院重症监护室(ICU)转来时,患者已经进行气管插管有创通气。因氧合恶化迅速、严重,我们建立了ECMO支持,随后从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找到了甲型流感、乙型流感、巨细胞病毒(CMV)、EB病毒共4种病毒和肺孢子菌(PC)。经过近4周竭尽全力的努力,ECMO的血流量降到1.5 L/min、氧流量甚至降到不到1 L/min,但始终也不能完全撤离,而T淋巴细胞计数一直没超过100个/微升。院内感染与ECMO撤离之间的博弈,最终前者先来一步,我们失败了,这也影响了此后患者的救治判断。
另一位51岁男性患者,因血小板减少以及长期激素治疗,考虑曲霉菌肺炎、呼吸衰竭,经当地医院ICU治疗迅速恶化而被转来,经急诊插管后氧合维持不住被收入RICU。有创通气用到了尽头;患者需要大剂量的药物维持血压;降钙素原>30 ng/ml,血小板只有2000个/μl。我们一度对继续抢救犹豫不决:参考过往,这样的患者即使上了ECMO,或院感,或出血,必死无疑。考虑患者年纪不大,家属信任理解,我们还是建立了ECMO,放手一搏。几经努力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一周后撤离ECMO,两周后恢复出院。如果开始时我们因觉得希望渺茫而选择保守呢?还是如果!
生活中有很多如果,一生很漫长,一次选择不满意,调整方向,努力再来一次;工作中有很多如果,生命很脆弱,一次选择不当,可能永远失去,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记得2004年的五一劳动节,在即将进入RICU工作前,王辰老师的一句话,我仍记忆深刻,不能稍有忘怀:“在这个ICU里,你们应该做到,如果患者不幸去世了,能拍拍自己的胸脯说,他的离去不是我们无能,是现代医学无能!”这句话就像对数函数的X轴和Y轴,可能永远不能完全企及,但我们不懈努力,争取无限接近,竭尽全力体现现代医学的救治水平!德不近佛不可为医,才不近仙不可为医。我们毕竟不是神佛,不能决定人的生死,但我们理应竭尽所能地帮患者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需要铭记的,也是一直践行的:生命可贵,别轻言放弃!
流感下的众“声”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屏后
本文逐日记录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29天阴阳两隔的经历。涉及就诊、用药、开销、求血、插管、人工肺(ECMO)等信息……从流感到肺炎,不是小病,是生命保卫战。——《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读完了《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我们能感受到什么?能悟出点什么来呢?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全民的健康教育,开展全民的爱国卫生运动,医疗卫生的改革必须是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燃眉之急的医改真是任重道远,努力吧!——网友芈尔
在梳理过程中,作者对于各种境遇的回忆、复杂的感觉和情感、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慢慢地超越了我对疾病诊治本身的关注,激发了思考。这是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自然转变,说到底医疗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社会活动,不单单是冰冷的科技。感谢家属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所记录的点点滴滴,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医学和人文。我们要珍视这种情感的叙述和对生命的思考,因为必须了解我们的伙伴和战友,才能共同面对前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李海潮
两万多字的长文,几乎未加剪裁的白描,几句点到为止的感慨,却让人看到生命与生活的双重脆弱,不免唏嘘。如何丰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何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如何增强家庭和个人的抗风险能力,都是需要破题之处。回看《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还有句医生说的话,值得深思:对病人来说,整体的治愈概率意义不大。毕竟,面临风险的是一位位个体,再小概率的风险,倘若降临到个体身上,也就成了100%。这或许也在提示我们:让整个社会充满生机,让一个时代安宁和谐,正需要让每一个生命都坚强、让每一段生活都坚固。这正是:治愈“流感焦虑”,仍须改革发力。——人民日报评论
思考与启示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一文在朋友圈引起了广泛共鸣,这篇以患者视角的就医历程,写尽了生命脆弱和人生无常,也道出了缺乏医疗常识家属的焦虑和防御心态。从普通人角度来说,如何通过平日科普积累必要的医学常识,关键时刻如何更理性地对待现代医疗?这样的需求日渐凸显,加强全民的健康教育成了当务之急。
然而,对于奋战在阻击流感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而言,在救治重症流感的日日夜夜里,有胜利的喜悦,更有生命难以挽救的惋惜和悲痛。这场流感疫情究竟带给我们临床医生哪些思考与启示?
解立新教授表示,“ECMO的有效应用为我们救治重症呼吸衰竭提供了重要的利器,明晰了重症感染与免疫失衡的根本关系,指引着我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整好行装,继续前行。”詹庆元教授则强调,“在流感高发的秋冬季节,医务人员须加强对流感病毒感染的识别能力,从而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应开展规范的呼吸支持治疗,早期给予抗病毒治疗,同时高度警惕曲霉菌属等合并感染的诊治。”
此外,如李海潮院长所言,医疗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社会活动,不单单是冰冷的科技。在医疗技术之外,我们或许应该去了解患者和家属在面对疾病时的焦虑、无助和绝望,走进他们的内心;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们要像孙兵教授一样,竭尽所能,帮助患者渡过难关,不轻言放弃。(邢英 整理)
(全文见附件PDF,《中国医学论坛报》)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