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作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宋海庆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系列文章导航
临床上新冠感染后认知障碍可根据英国国家卫生和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UK NICE)提出的诊断标准进行临床诊断:
经实验室检查确认的新冠感染;
在新冠感染期间或之后出现认知功能减退(记忆力、语言、定向力、应用、注意力、知觉和执行能力等减退),持续超过12周,不能用其他疾病解释。
目前基于相关证据可将新冠感染相关认知障碍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仅表现为认知障碍,具有记忆、语言、定向、应用、注意力、知觉(视、听、感知)和执行功能障碍等症状,提示新冠感染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
另一类为脑雾,是一种“大脑模糊状态”,是新冠感染后常见的神经系统症状。脑雾是一系列症状的集合,表现为认知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失语、健忘等),同时可能伴有疲劳、缺乏动力和睡眠障碍等。脑雾并不一定伴有大脑的结构性损伤,大部分“脑雾”会在1个月~1年之内逐步缓解。
临床文献有大量报道新冠感染相关认知障碍。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在新冠感染诊断3个月及以上的个体中,22%出现认知障碍[2]。在另一项针对新冠感染后神经精神症状的荟萃分析中发现,脑雾(brain fog)约占32%,记忆障碍27%,注意力障碍22%,说明认知障碍在长病程新冠感染中广泛存在[3]。一项针对武汉老年新冠感染患者(>60岁)的1年认知变化轨迹的纵向队列研究表明,出院后12个月患者认知障碍的发生率为12.45%,并且重症COVID-19组12个月时的认知评分低于非重症组和对照组[4]。
COVID-19严重程度、谵妄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目前认知障碍(current cognitive impairment)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低、重症COVID-19、谵妄、高血压、COPD是纵向认知功能减退(longitudinal cognitive decline)的危险因素[5]。
认知障碍患者的新冠感染风险也显著高于认知正常人群。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感染新冠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2.29倍,痴呆患者感染新冠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2.16倍[6]。新冠感染前已存在认知障碍相关基础疾病的人群症状更易加重,具体是指在新冠感染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变性病和非变性病引起的认知障碍。
变性病主要包括AD、路易体痴呆(DLB)、帕金森病痴呆(PDD)和额颞叶变性(FTLD)等。
非变性病主要包括血管性痴呆(VaD)、正常压力性脑积水以及其他疾病,如颅脑损伤、感染、免疫、肿瘤、中毒和代谢性疾病等。
痴呆患者在新冠感染最初阶段常有精神状态改变等不典型新冠感染症状(包括意识混乱、焦虑、迷失方向、拒绝照料和食欲缺乏等),而发烧和咳嗽等典型症状往往滞后,造成诊断和治疗的延误。因此,对此类患者应该提高警惕。
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SARS-CoV-2感染和帕金森病(PD)之间存在相关性。病例报道通常在SARS-CoV-2感染后2~5周内出现临床PD,影像显示了PD的典型征兆,但无前驱症状及相关家族史,基因检测未发现PD风险变异,予传统的多巴胺能药物治疗后PD症状减轻,其中一例患者未经药物治疗后自行恢复。
在并存糖尿病、痴呆症或高血压等疾病的情况下,血管内皮细胞ACE2表达增加,进而与SARS-CoV-2 S蛋白的S1亚基结合[7, 8]。对急性COVID-19患者的神经影像研究报告了海马区各向异性分数和扩散性的破坏,这表明海马内的微观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变化[9]。海马是大脑中对记忆形成至关重要的区域,也参与了调节焦虑和应激反应的皮质下网络。与此一致的是,对急性感染患者的尸检研究发现,海马区的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分别表达IL-1B和IL-6,已知这些细胞因子调节海马亚颗粒带(SGZ)内新神经元的产生,而SGZ是情节记忆和空间记忆形成所必需的。SARS-CoV-2感染还会对丘脑产生抑制作用,丘脑失调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可能以丘脑内功能改变或与驱动情绪、动机、认知、睡眠、疼痛、觉醒和运动活动的关键大脑区域的功能连接的形式出现[10]。
一项研究揭示了“脑雾”关键的致病机制,研究发现,受SARS-CoV-2感染的小鼠,在病毒被清除之后,体内的“嗜酸性粒细胞趋化蛋白(CCL11)”细胞因子在血液和脑脊液中都增加了,这个变化在感染后的7周仍然存在。CCL11是一种与神经发生和认知障碍有关的趋化因子,也是衰老的标志物,它的升高与认知能力减退相关[11]。但目前尚无研究能够明确SARS-CoV-2感染和“脑雾”之间的因果性。在临床造成这种“脑雾”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慢性疲劳综合征、缺铁性贫血等疾病都会导致“脑雾”的发生。
目前认为在SARS-CoV-2感染期间发生的神经炎症与AD显著相关。基于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PPI)和CRISPR-CAS9的遗传分析,结果发现COVID-19宿主蛋白和基因显著影响与AD相关的蛋白和基因的表达,包括RAB7A、TGFB1和VCAM1。
此外,在新冠感染患者的脑脊液和血液中还检测到AD生物标志物NKTR3、GSTM3、TGFB1、TNFRSF1B、SPP1和CXCL10的异常表达。该研究得出结论,SARS-CoV-2感染和AD之间存在显著的机制重叠[12]。SARS-CoV-2感染引起的血管并发症和炎症是与PD进展相关的标志。SARS-CoV-2的神经侵袭性也可能是与PD发生相关的一个潜在因素。研究发现,SARS-CoV-2会影响纹状体,其主要的机能是调节肌肉张力、协调各种精细复杂的运动。如纹状体受到损害,则其功能发生障碍,这也可能与PD发生相关。
SARS-CoV-2感染对大脑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尚不完全清楚,但足够的证据表明它是脑损伤和神经退化的潜在风险因素。前瞻性的纵向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SARS-CoV-2感染在包括AD和PD在内的神经变性疾病进展中的持久影响至关重要。
另外,嗅球内的慢性炎症会影响感觉、情绪和认知过程。嗅球在功能上与控制食欲、感觉、情绪和认知反应的边缘系统相连,因此可以影响边缘系统的活动。这些发现表明,感染后的行为变化可能与嗅觉通路的炎症存在因果关系。研究显示,慢性嗅上皮神经和嗅球炎症可能驱动神经变性和与长新冠症状一致的结构变化[10]。
中国武汉一项回顾性病例研究的结果显示,有0.5%的患者出现了癫痫发作[13]。此外,也有COVID-19患者以癫痫为首发症状。对于既往有癫痫病史且经药物控制良好的患者,出现癫痫症状突然加重时,也要考虑到感染性疾病包括COVID-19的可能[14]。
病毒感染后癫痫发作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它们要么是由于病毒直接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要么是由于炎症细胞因子的增加而继发的,炎症细胞因子然后可以激活谷氨酸受体,导致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和急性癫痫发作。在这一点上,新冠感染期间升高的IL-6水平可能有助于癫痫的发生,因为此前升高的IL-6水平与热性癫痫有关。在大鼠模型中,鼻内注射IL-6显示癫痫发作加剧。
RAS系统可能参与触发癫痫发作。颞叶癫痫患者海马中Ang II、AT1R和AT2R受体的表达上调[15]。持续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可预防癫痫大鼠模型的癫痫发作[16]。在COVID-19中ACE2可获得性降低,Ang II及其下游的促炎介质水平升高,可能参与了癫痫的发生。
此外,COVID-19相关并发症,如缺氧、代谢紊乱、细胞因子风暴和卒中也可能参与癫痫的发展。但癫痫通常是作为脑炎、脑病等并发症的症状而被记录。
新冠感染患者发生脑病的风险相对较高。脑病是指由于大脑局部或广泛受损导致的精神状态改变而影响脑的高级神经功能和兴奋性的临床综合征,其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于全身性疾病的脑损害。脑病/脑炎在老年患者中更常见,并指出这些患者病情严重。考虑到新冠感染患者中脑病的广泛报道,进一步研究导致脑病的机制至关重要。
COVID-19引起的病毒血症、代谢障碍、器官功能障碍等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可以造成脑组织损伤而导致脑病,包括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急性出血坏死性脑病(AHNE)、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PRES)、高血压脑病。
低氧血症已经成为新冠感染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因此,脑病还可以通过感染期间表现出的低氧状态启动的另一种途径进行。HIE可能是由于大脑中氧气灌流不足和葡萄糖供应不足导致脑组织无氧代谢所致。由此产生的低细胞pH值引起脑血管扩张、脑水肿、脑血流受阻和脑缺血。基底节、海马结构、小脑和丘脑是介于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之间的大脑区域,已被报道为HIE特异性和极大的影响区域。
AHNE可能与COVID-19诱发的过度激活炎症反应有关,进而引起血脑屏障破坏。
PRES也是COVID-19相关脑病的表现之一,在影像学上可见到顶枕部脑实质的血管性水肿征象。
血压波动可能参与了PRES和高血压脑病的发生,可能与SARS-CoV-2和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ACE2结合后引起的内皮功能障碍和血脑屏障自我调节功能紊乱有关[17]。
此外,血压的急剧升高会导致毛细血管上的直立性血浆渗漏,再加上血脑屏障的破坏,就会引发一系列可能导致高血压脑病的事件。在新冠感染患者中,SARS-CoV-2降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的表达,增加发生ACE依赖性高血压的风险。因此,临床医师应加强对COVID-19患者的血压管理。
神经痛、肌痛和骨骼肌损伤、格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颅神经病、神经肌肉接头疾病、神经眼科疾病、感音神经性听力丧失和自主神经异常已被报道为COVID-19患者的周围神经系统(PNS)表现。累及PNS可能是由于SARS-CoV-2导致的免疫失调。COVID-19患者可能出现系统性高炎症伴巨噬细胞激活综合征,也称为继发性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18]。这些免疫介导的表现通常发生在感染急性期消退之后[19]。
中国武汉一项回顾性病例研究的结果表明,重症和非重症新冠感染患者分别有4例(4.5%,88例)和1例(0.8%,216例)出现神经痛;重症和非重症新冠感染患者分别有17例(19.3%)和6例(4.8%)出现骨骼肌损伤[13]。值得注意的是,肌酸激酶(CK)升高作为肌肉损伤的唯一标志的报道是非特异性的,可能与严重新冠感染病例的长时间卧床休息和药物治疗有关,而不是与新冠感染的直接肌肉损伤有关。在其他已发表的研究中,有15.79%到100%的COVID-19患者有肌痛的报道[20-33]。
肌炎可以是新冠感染的一种表现,尽管大多数文献只涉及病例报告。COVID-19可能是肌炎的触发因素,暴露在病毒中可能会由于分子模拟而发生自身免疫反应[34]。
最近的证据表明,新冠感染还可能导致多种颅神经疾病。伴随病毒感染的嗅觉丧失更是高发,感染者中高达73%[35]。但与其他哺乳动物不同的是,嗅觉感受器神经元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会被替换,它们不断从未分化的基底细胞再生,这解释了SARS-CoV-2相关的嗅觉症状可能不是永久性的。
COVID-19感染后也可能发生新发重症肌无力(MG),也可能与其他神经学表现一样,由分子拟态机制引起。有证据表明COVID-19还可以通过增强T细胞信号通路引发自身免疫。COVID-19中出现的急性呼吸窘迫(ARDS)加上MG危象中的呼吸肌衰竭可能导致可怕的预后。
据报道,COVID-19患者还出现了听觉并发症。在一项自我报告调查中[36],对出院8周后患有严重COVID-19听力和(或)耳鸣症状的138名成年人进行了随访,16例(13.2%)患者报告在COVID-19诊断后听力和(或)耳鸣发生变化。然而,在COVID-19中,听觉并发症是罕见的表现。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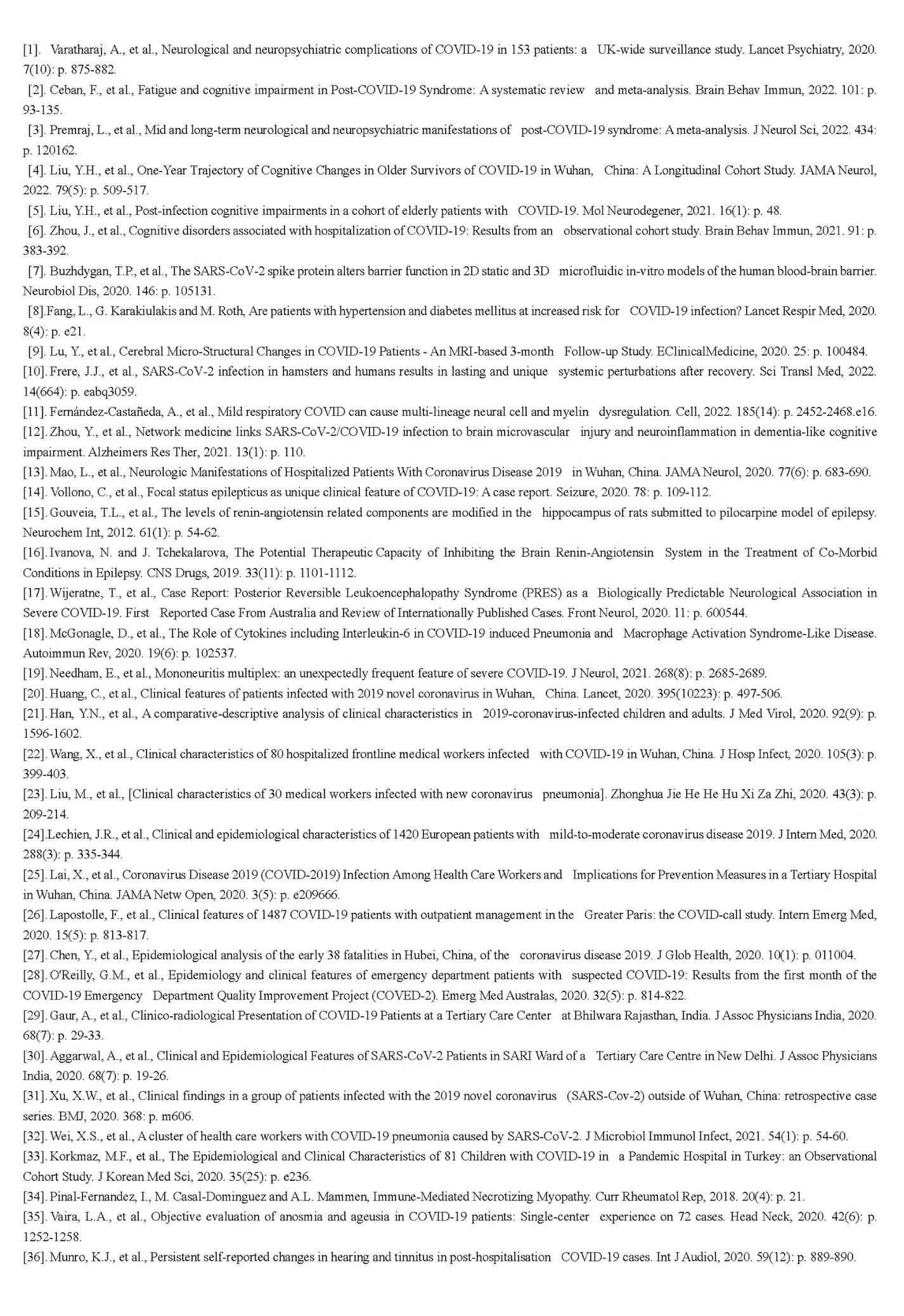
中国医学论坛报版权所有,转载须授权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