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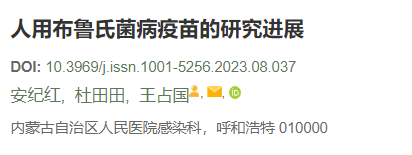


布鲁氏菌是由布鲁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疾病。布鲁氏菌属于革兰阴性、兼性、细胞内病原体,通过食用受感染的、未经巴氏灭菌的动物奶和奶制品,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部位,皮肤和黏膜破裂或吸入受感染的雾化颗粒而传播给人类[1]。布鲁氏菌的临床表现多样,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年,临床误诊率高,因此往往发生治疗不足和病程延长。主要反应为发热、疲劳、关节痛和肌肉疼痛。成人和儿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皮疹、呼吸和心脏并发症以及睾丸炎/附睾炎在儿童患者中更为普遍。布鲁氏菌的常见并发症是肝炎,其次是骨关节炎、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噬血细胞综合征和男性睾丸炎及附睾炎[2]。布鲁氏菌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是高度动态的,可随着新的感染区域的出现和感染在早期存在感染的地区再次出现[3]。布鲁氏菌呈全球性分布,地中海、欧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墨西哥、非洲、近东国家等地区多见。近年来,在中亚和中东国家出现了新的人类布鲁氏菌患病地区,患病率不断上升[4]。虽然布鲁氏菌是最普遍的人畜共患病,但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归类为“罕见病”,适用于患病率较低的大多数发达国家[5]。目前,美国每年报告新增布鲁氏菌病例<100例(患病率0.4/100万),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南部和西南部,病源为自墨西哥非法进口的软奶酪(未经高温消毒)[6]。其真实患病率预计为实际报告例数的5~12倍,且均为食源性疾病[7]。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报告显示,叙利亚布鲁氏菌患病率最高(1 603.4/100万),其次为蒙古(3 910/100万)、伊拉克(268.8/100万)、塔吉克斯坦(211.9/100万)、沙特阿拉伯(149.5/100万)和伊朗(141.6/100万)[8-9]。


仅有少数抗生素能够进入布鲁氏杆菌细胞壁,进而有效遏制细菌。目前,临床治疗人类布鲁氏菌的抗生素包括:四环素、甲氧嘧啶-磺胺甲恶唑、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利福平、喹诺酮和氯霉素[10]。上述单药治疗后复发率高达5%~40%[11],因此临床往往采用多药联合治疗。


随着DNA重组技术的发展和布鲁氏菌基因组序列的完成,众多研究开始着眼于寻找更安全、更有效的疫苗[12]。初步研究[13-15]表明,新疫苗类型主要包括基因工程减毒疫苗、亚单位疫苗和其他潜在疫苗,均具有更高的保护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布鲁氏菌灭活疫苗虽然安全性较高,但难以诱导有效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也不能有效激活细胞免疫应答。近年来新型疫苗的研究不断涌现,包括载体疫苗、DNA疫苗、外膜囊泡疫苗、纳米颗粒疫苗等,但这些疫苗多数仍处于研究阶段,而且面临着免疫效果不佳、免疫保护时间较短、成本较高、工艺复杂等诸多挑战[16]。与此相比,减毒疫苗可以更有效地激发机体的细胞免疫应答,产生的保护力也更持久[17],且减毒疫苗通常具有生产工艺简便、成本较低等优点。常规的布鲁氏菌减毒疫苗主要是通过筛选毒力较弱的布鲁氏菌分离株或是对布鲁氏菌分离株和强毒菌株进行连续传代致弱得到的[18]。
人用布鲁氏菌疫苗的研制较为困难,国外尚未有疫苗上市,我国唯一获批的人用布鲁氏菌疫苗为减毒活疫苗104M株[19]。104M是一种皮上划痕接种的减毒活疫苗,分离自前苏联地区感染布鲁氏菌的胎牛体内,经连续传代减毒获得[20]。自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使用以来,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一定验证,但是仍然存在划痕接种复杂、疫苗免疫机制不明确、存在残余毒力等问题。人用布鲁氏菌疫苗研制困难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布鲁氏菌存在多个种型,且保护性抗原谱复杂,单一抗原很难发挥完全的保护作用[21]。流产双歧杆菌104M自1965年获得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以来,已在我国广泛用于控制和预防人类布鲁氏菌。104M疫苗表现出生物型的典型性质,对实验动物的低且稳定的毒力以及强大的免疫原性。流产双歧杆菌菌株S19(在我国也被称为A19)可感染人类,引起布鲁氏菌的典型特征,最初于1923年作为毒力菌株从泽西岛奶牛身上分离出来。可在胰蛋白酶大豆肉汤[37 ℃下连续振荡(220 r/min)]中培养流产双歧杆菌[22]。
亚单位疫苗是目前对于布鲁氏菌感染保护性较高的一种疫苗,国外相关研究人员对亚单位疫苗的制备采取了L7/L12[23-24]等特殊方法,使其成为目前高效性最强的疫苗。此外,亚单位疫苗的成分比较单一,主要包括布鲁氏菌外膜蛋白、包质结合蛋白,L7/L12蛋白以及胞质结合蛋白P39等[25],简单的成分使亚单位疫苗的安全性更高,这些优势使其在临床上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26-27]。
目前,关于布鲁氏菌各型疫苗的研制已经成为了当下的研究热点,尤其以多种合成途径为靶点研发的一系列疫苗研究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28],但在研疫苗普遍存在稳定性差、保护期短、免疫重复等不足。相较于减毒活疫苗[29],亚单位疫苗不良反应低,对血清学监测不产生干扰;同时,由于布鲁氏菌的同源性高,亚单位所产生的保护性覆盖面较广,1种亚单位疫苗即可对抗多种型别的布鲁氏菌株的感染。目前,亚单位疫苗尚未推广应用,因大多数布鲁氏菌疫苗未能达到目标要求的保护性,或与疫苗载体种类的选择或者改良有关[30],也可能与所需的保护性免疫应答的佐剂识别的缺乏有关。
通过使用乳酸球菌和克林病毒载体可以诱导机体产生免疫性保护。有研究[31]利用重组痘苗病毒诱导小鼠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反应,但该免疫性对布鲁氏菌抗原所产生的保护性水平并未达到预期。自此,相关研究调整方向,发现布鲁氏菌感染多数发生在黏膜水平,而黏膜途径的免疫方法可以激发大量的淋巴细胞对抗感染,并非依靠T淋巴细胞亚群维持免疫应答[19]。基于此,在未来研制目标疫苗最大的挑战在于人体内激发出能够产生强烈的细胞免疫反应。因此,这一实验证明了通过诱导IL-12和INF-γ对宿主免疫系统产生细胞反应可以产生较好的保护性。
布鲁氏菌的生长方式是胞内寄生,理论上如果能够提高患者对于特异性细胞所产生的介导免疫反应,即可控制布鲁氏菌的感染。目前,DNA疫苗能够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反应,且DNA疫苗具有安全性高、稳定性强、制作方法较简单、成分低等多种优势,现已成为布鲁氏菌疫苗研究的热点[32]。


布鲁氏菌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威胁人类健康和造成贫困的七大“被忽视的人畜共患病”之一[33]。作为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细菌性疾病,布鲁氏菌主要从动物传播给人类,每年约有50万例新发人类感染病例。目前,仅接种疫苗无法满足预防需求,需要监测和屠宰受感染动物控制布鲁氏菌的发生发展[34]。然而,由于最具保护性的疫苗可能影响血清学监测结果,进而影响及时诊断,最终可能导致布鲁氏菌防控和治疗的失败[35]。通过检测光滑脂多糖的布鲁氏菌细胞壁O-多糖(OPS)成分的抗体,可用于该病的诊断,该分子对目前部署的兽用全细胞疫苗具有重要的保护功效。这引发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悖论,即虽然布鲁氏菌OPS赋予疫苗保护功效,但存在导致受感染和接种疫苗的动物具有相似的抗体谱。因此,不可能将感染者与接种疫苗的动物(DIVA)区分开来,限制了该疾病的预防性诊疗[36]。最近研究[37]表明,布鲁氏菌OPS作为2个寡糖序列的嵌段共聚物,为利用仅在该疾病的血清学测试中通过化学合成获得的独特寡糖提供了机会。与当前商业测试中使用的天然聚合物相比,这些寡糖显示出优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有助于鉴别布鲁氏菌与由几种具有OPS的细菌引起的感染。在这些合成抗原的合成和免疫化学评估过程中,很明显存在创造多糖-蛋白质偶联疫苗的机会,该疫苗不会产生在感染诊断测试中出现假阳性结果的抗体[38]。这一目标在被简化的小鼠免疫实验[39]中表明,在基于M抗原的诊断测试中,可以在不反应的情况下开发布鲁氏菌A抗原抗体。这种类型的结合疫苗可以很容易地开发用于人类和动物。然而,随着化学方法的进步和现代细菌工程方法的成熟,预计这些研究阐明的原理可以应用于开发一种廉价且具有成本效益的疫苗,以对抗动物地方性布鲁菌病[40]。


布鲁氏菌主要是发展中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地方性疾病。受当前卫生、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影响,布鲁氏菌的流行率正在上升[41]。目前,布鲁氏菌疫苗相关研究重点应着眼于潜在的候选疫苗、DNA疫苗的能力、易于给药的载体疫苗以及几种重组和亚单位疫苗。虽然接种疫苗可能是最合适的疾病控制措施,但致病性布鲁氏菌属在许多其他牲畜或野生动物中的持久性可能导致预防失败,或者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类感染。因此,开发在野外条件下高效和安全的新型疫苗,解决宿主物种的多样化问题,同时改善布鲁氏菌监管计划的其他组成部分,可能对世界范围内防控布鲁氏菌的人类感染流行发挥更大作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