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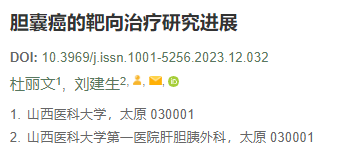
胆囊癌(gallbladder cancer,GBC)是胆道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占胆道肿瘤的2/3左右,5年生存率仅有5%[1]。该病早期无特殊表现,当患者出现上腹部疼痛、腹胀甚至黄疸等非特异性症状时,通常表明肿瘤已经处于进展期[2]。迄今为止,外科手术是GBC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因其恶性程度高,易发生血行转移和淋巴转移,并直接侵犯肝脏,故根治性手术对于晚期GBC疗效有限[3-4]。此外,由于GBC容易产生放化疗耐药性,放化疗等综合治疗效果也不佳[5]。
靶向治疗是一种根据细胞或分子表面明确的致癌位点设计相应的靶向药物,药物进入体内特异性地选择相应的靶向位点结合发挥作用致使癌细胞死亡的治疗方式[6-7]。近年来,随着对GBC潜在致病机制的深入研究以及测序技术如二、三代测序、人类全基因组测序、RNA测序及表观遗传学和代谢组学分析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基因突变位点被发现,并开展了针对不同靶点的药物临床试验[8]。本文旨在通过回顾GBC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对相应的通路及靶向治疗药物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期为GBC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该通路包括ErbB1、ErbB2、ErbB3和ErbB4,也称为HER1(EGFR)、HER2、HER3和HER4,即HER家族。ErbB基因是细胞表面受体,具有跨膜酪氨酸激酶结构域,能够与表皮生长因子结合激活多个下游信号通路。Li等[9]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等发现,ErbB通路是GBC最广泛的突变通路,影响36.8%的样本。本文将以ErbB1和ErbB2为例具体介绍。
ErbB1也称HER1或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是一种Ⅰ型受体酪氨酸激酶。EGFR在细胞生长、增殖、分化、迁移中起关键作用并抑制细胞凋亡,通过激活多种细胞下游信号通路发挥作用,包括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rotein kinase B/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PI3K/Akt/mTOR)等途径。
目前针对EGFR的药物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与EGFR胞外结构域结合的单克隆抗体(EGFR-mAb),主要包括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通过抑制下游信号通路从而阻止EGFR二聚体活化发挥作用;第二类是通过与ATP竞争结合EGFR胞内酪氨酸激酶并间接抑制其功能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主要包括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阿法替尼,目前已经改进至三代EGFR-TKI药物来对抗EGFR的突变活性[10-11]。
Mody等[12]报道了1例Ⅳ期GBC患者,在接受口服EGFR-TKI联合化疗治疗后,患者CA19-9恢复正常,PET/CT显示疾病完全缓解;Lubner等[13]的一项10例GBC患者多中心Ⅱ期试验报告:厄洛替尼和贝伐珠单抗联合显示出临床活性,且很少出现3~4级不良反应,这些实验结果均为使用EGFR-TKI治疗GBC提供了依据;Chen等[14]的试验说明加用西妥昔单抗并没有显著提高吉西他滨联合奥沙利铂(GEMOX)化疗治疗GBC的客观缓减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但有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的趋势。此外,Cai等[15]通过荟萃分析评估了EGFR靶向药物GEMOX在胆道癌中的联合治疗:与单独使用GEMOX相比,GEMOX和EGFR靶向药物的组合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没有显著差异(P=0.39),但是改善了PFS(P=0.03);EGFR-TKI和EGFR-mAb相比,EGFR-TKI组获得了更好的ORR。
ErbB2也称HER2,是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可介导MAPK通路及PI3K/Akt/mTOR通路,参与细胞生长、存活、黏附、迁移和分化[16]。对108例中国和107例美国GBC患者进行了全面的基因组分析后,Yang等[17]发现基因ErbB2突变在中国患者中占18.5%,在美国患者中占13.1%。目前针对ErbB2靶向治疗的药物主要包括: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拉帕替尼、来那替尼和阿法替尼等。
Kiguchi等[18]试验发现ErbB2在胆道上皮基底层的过表达可导致100%的转基因小鼠在3月龄前发生胆囊癌,证实ErbB2是胆囊癌的原癌基因。近年来相关临床案例中,Jeong等[19]通过一项前瞻性研究说明曲妥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GC)化疗方案在HER2阳性GBC患者中ORR为50%,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为100%,这项试验虽然只有4例样本,但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参考;Lee等[20]在一项34例患者多中心Ⅱ期试验中对曲妥珠单抗联合奥沙利铂+亚叶酸钙+氟尿嘧啶(FOLFOX)治疗GC难治性HER2阳性胆道癌进行研究,结果显示:DCR为79.4%,中位PFS(mPFS)为5.1个月;中位OS(mOS)为10.7个月,此研究表明,对于HER2阳性胆道癌,曲妥珠单抗联合FOLFOX方案治疗显示出良好的效果,且不良反应可接受,值得进一步研究。综合现有的试验,如何选择GBC的靶向药物还需进一步探索,同时使用靶向药物前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基因检测,可以很大程度上为用药提供参考,提升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重要的血管生成调节因子,参与伤口愈合、血管生成及血管通透性改变,VEGF的过表达与晚期肿瘤增殖、侵袭和转移相关[21]。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抑制剂可与VEGF结合,从而竞争性减少VEGF与VEGFR的结合,抑制微血管生成,与之相关的药物有:贝伐珠单抗、雷莫芦单抗、索拉非尼、舒尼替尼、索凡替尼等。
Zhu等[22]的一项纳入10例GBC患者的Ⅱ期试验评估了贝伐珠单抗与GEMOX联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实验结果为联合用药组mPFS为7个月,OS为12.7个月,均高于单纯化疗组;在Iyer等[23]的一项多中心的Ⅱ期临床试验中,11例GBC患者使用贝伐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卡培他滨(GEMCAP)治疗的mPFS为8.1个月,mOS为11.3个月,同样高于单纯化疗组;此外,Xu等[24]在包括5例GBC在内的39例胆道癌患者中进行了索凡替尼的研究,患者mPFS为3.7个月,mOS为6.9个月,说明索凡替尼单药治疗胆道癌的临床疗效中等,耐受性和安全性良好。然而Bengala等[25]通过包括14例GBC在内的46例胆道癌患者研究得出结论:索拉非尼单药治疗毒副作用较小但活性低:PFS为2.3个月,mOS为4.4个月。
截止目前,可以初步得到VEGF/VEGFR与化疗药物的联合应用比单纯化疗有效性更高的结论,但仍需要进行更多的病例对照研究来更好地阐明这些方案的确切功效。
由ErbB和VEGF激活的PI3K/Akt/mTOR信号通路参与多种细胞生理过程,包括细胞生长、迁移、分化和细胞凋亡等,与多种癌症的发病机制有关[26]。该通路的异常,例如PI3K突变、PI3KCA扩增、磷酸化Akt(p-Akt)和p-mTOR异常,均与GBC的预后相关[27]。针对该通路常用的药物有:PI3K抑制剂(copanlisib)、Akt抑制剂(MK-2206)以及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everolimus)。
PI3K/Akt通路的激活会增加化疗耐药性,因此使用PI3K通路抑制剂可以辅助治疗。Tan等[28]一项纳入包括3例GBC在内的24例胆道癌患者的Ⅱ期试验评估了PI3K抑制剂copanlisib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在GC方案的基础上加用copanlisib未能改善患者6个月的PFS,但是试验结果与PI3K/Akt/mTOR通路调控的抑癌基因PTEN表达相关:与PTEN高表达的患者相比,copanlisib联合GC方案改善了PTEN低表达患者的PFS和OS,两组的mOS分别为7.0个月和17.9个月,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PTEN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mTOR是PI3K/Akt信号通路的下游介质。针对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的Ⅱ期临床研究[29]结果显示,依维莫司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14例GBC患者mPFS为6.0个月,mOS为9.5个。Costello等[30]对依维莫司加吉西他滨两种药物方案和依维莫司加GC三种药物方案进行了Ⅰ期试验,以确定两种联合方案的最大耐受剂量,并对胆囊胆管癌患者进行在最大耐受剂量内的治疗,结果显示,在纳入的10例患者中,6例患者病情稳定,4例进展,故这三种药物的联合应用可以作为未来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
综上,由于样本量较少,将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应用于临床之前仍需要更多的试验数据支持。此外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联合化疗,用药前对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增加这些药物的靶点特异性将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MAPK信号通路是一条重要的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RAS/RAF/MEK/ERK是该通路中最常见的途径,可调节各种细胞活动,但在癌症中经常失调。多种癌细胞通过该通路促进癌细胞的增殖、代谢和转移并抑制凋亡,导致肿瘤发生。对此目前常用的抑制剂有曲美替尼、司美替尼和索拉非尼等。
Kim等[31]的一项纳入14例GBC患者关于曲美替尼的前瞻性Ⅱ期试验中,治疗组mPFS为1.4个月,mOS为4.3个月,患者对曲美替尼耐受性良好,但有效性不高;此外,一项多机构对包括7例GBC在内的胆道癌患者的Ⅱ期研究[32]表明,口服司美替尼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可耐受性,该研究中患者mPFS为3.7个月,mOS为9.8个月。
近年来,关于GBC中PI3K/Akt/mTOR及MAPK通路上游靶点的研究日渐突出,大量基础实验[33-36]验证了许多影响此通路的新靶点,如KIF11、miR-4461、KIR3DL3、SIRT3等,可影响GBC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等活动,值得进一步探索。
随着免疫治疗的快速发展,T淋巴细胞表达的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在GBC中的作用机制也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研究[37]。目前较常用的相关药物有:派姆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德瓦鲁单抗和曲美单抗。
派姆单抗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它与PD-1受体结合,从而阻断其与其配体、PD-L1和PD-L2的相互作用[38]。Piha-Paul等[39]研究发现,无论PD-L1表达如何,派姆单抗单药治疗对晚期胆道癌患者均具有持久的抗肿瘤活性,且毒性可控;同时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Kang等[40]发现对12例PD-L1阳性GBC患者使用一线GC方案后疾病进展,再使用派姆单抗可产生抗肿瘤活性;Kim等[41]使用纳武利尤单抗治疗54例难治性胆道癌,mPFS为3.68个月,mOS为14.24个月,可见患者对纳武利尤单抗有良好的耐受性和适度的疗效。
关于GBC与PD-1/PD-L1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对未来GBC的治疗有指导价值。免疫检查点阻滞剂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影响下一步临床治疗方案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并希望在未来开展更多临床试验来评估这些分子在GBC中的治疗价值,以探寻到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GBC是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目前尚无标准的治疗方案,靶向药物的出现为GBC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成为治疗GBC的新方法。由于个体基因具有差异性,不同患者对药物的反应各不相同,因此努力探索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联合不同途径的靶向治疗或将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相结合,以及尽可能通过基因检测对患者进一步精细化分组,并制订个体化诊疗方案应当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此外,一些其他的研究如类器官模型和液体活检技术也有助于提高药物敏感性并对产生耐药性突变的基因进行筛选,为靶向治疗提供指导作用,有助于后续的研究。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