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肝病,特点是转氨酶升高、自身抗体阳性、免疫球蛋白G(IgG)升高、组织学上表现为界面性肝炎[1]。男女患病比例为1∶4~1∶6,但男性患者的数量逐渐增加,特别是2004年日本的男女比例为1∶7,2016年增加到1∶4[2]。AIH在全球的年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为1.37/10万人和17.44/10万人,研究[3]还表明,年龄≥60岁的人更易患AIH,这与经典的AIH主要影响青年和中年妇女的描述相反。
AIH的确切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个体的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对肝抗原耐受的丧失有关[4]。早期诊断和治疗AIH很重要,目前推荐的一线治疗为泼尼松(龙)(prednisone/prednisolone,PRED)联合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或PRED单药治疗,对标准治疗反应欠佳或对副作用不耐受的患者可采用替代疗法。本文对目前AIH的药物治疗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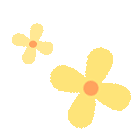
一线治疗的目的是改善症状,预防疾病进展,达到生化缓解,减少并发症,理想的生化缓解是血清转氨酶和IgG水平的正常化[5]。
20世纪70~80年代的试验为免疫抑制治疗AIH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些研究是在发现丙型肝炎病毒之前进行的,因此很可能包括病毒性丙型肝炎患者[6]。有研究[7]表明,即使在肝硬化阶段,免疫治疗也能导致肝纤维化的消退。
美国肝病学会(AASLD)2019年指南[5]建议单独使用PRED(成人40~60 mg/d,急性重症患者60 mg/d);或PRED(20~40 mg/d),与AZA联合(AZA成人剂量: 50~150 mg/d),每1~2周进行生化检验。欧洲肝病学会(EASL)2015年指南[6]建议PRED起始剂量为0.5~1 mg·kg-1·d-1,两周后加入AZA 50 mg/d,并根据毒性和反应而增加,直到维持剂量为1~2 mg/kg。我国2021年指南[8]建议将PRED+AZA作为初始一线治疗方案,PRED初始剂量为0.5~1 mg·kg-1·d-1(通常30~40 mg/d),诱导缓解方案:PRED 30 mg/d 1周、20 mg/d 2周、15 mg/d 4周,PRED剂量低于15 mg/d时,建议以2.5 mg/d的幅度渐减至维持剂量(5~10 mg/d);维持治疗阶段甚至可将PRED完全停用,仅以AZA 50 mg/d单药维持。
联合治疗可显著减少PRED剂量及其不良反应,尤其适用于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糖尿病、肥胖、痤疮、情绪不稳以及高血压患者。关于加用AZA治疗的时间尚不明确,AASLD和EASL指南有不同建议。一项研究[9]表明, 早期(<2周)和延迟(≥2周)引入AZA,患者转氨酶正常化率和生化缓解率没有差异,停药率和疗效与AZA起始时间无关。
有研究[10]提出低剂量类固醇也可以诱导AIH缓解,研究把451例成人患者分为高剂量组(0.50 mg·kg-1·d-1,n=281)和低剂量组(<0.50 mg·kg-1·d-1,n=170),两组患者1年后生化缓解率相似(76.2% vs 77.6%),与类固醇相关的不良反应也相似,而低剂量组可显著降低PRED的不必要暴露。这一研究表明大剂量类固醇并非AIH缓解的必要条件,但仍需更多的研究支持。
虽然免疫抑制治疗非常有效,但长期服用有严重的副作用,因此,在达到临床缓解后应考虑停药。AIH的缓解包括生化缓解和组织学缓解,生化缓解如前所述,组织学缓解包括界面性肝炎的消失,通常在血清学缓解后很久才出现,即使血清转氨酶和IgG均恢复正常,仍经常存在界面肝炎残留,导致AIH停药后复发[11]。因此,EASL指南[6]建议:AIH治疗应持续至少3年,并在血清转氨酶和IgG水平完全正常化后至少2年,可以考虑终止治疗,停药前进行肝组织学检查可以排除未知的炎症和减少复发率;当AIH复发时,治疗方案与初始治疗方案相同,且同等有效。
布地奈德是第二代糖皮质激素,在肝脏的首过清除率约90%,其药物代谢和作用与泼尼松相似,但其主要部位为肠道和肝脏,全身不良反应较少[8]。Manns等[12]比较了布地奈德联合AZA与标准治疗的效果,布地奈德治疗开始时为3 mg,3次/d,当患者达到临床缓解时降低到3 mg,2次/d,PRED起始剂量为40 mg/d,在第9周通过固定模式降至10 mg/d,两组均给予AZA 1~2 mg·kg-1·d-1。结果表明布地奈德组明显有更多的患者达到主要终点生化缓解(47% vs 18.4%),类固醇特异性副作用的发生率降低约40%。但此研究PRED的起始剂量低于常用剂量,且遵循严格的减量模式,而布地奈德的减量取决于治疗的反应。这可能解释了本研究中标准治疗生化缓解率极低(38.8%)的原因。一项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13]显示,布地奈德组和泼尼松组的生化缓解率(16% vs 15%)和类固醇副作用的频率(47% vs 63%)没有显著差异,除了布地奈德组平均体质量增加较低外。
因此,AASLD指南[5]建议对于患有AIH但无肝硬化或急性严重AIH的儿童和成人,布地奈德联合AZA可作为一线治疗,对于肝硬化患者,因为门体分流失去首过效应的优势,布地奈德进入体循环可加重类固醇特异性副作用,同时有门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

二线疗法用于标准治疗失败、不完全反应和药物不耐受的患者,治疗失败发生在7%~9%的成人中[5]。二线疗法包括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嘌呤抑制剂、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s,CNI)和甲氨蝶呤等。
MMF是麦考酚酸的衍生物,可以抑制肌苷-磷酸脱氢酶,从而抑制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的增殖[1]。在对AZA不耐受或对标准治疗反应不理想的患者中,MMF是AIH二线治疗的首选药物。
一项研究[14]纳入126例成人AIH患者接受PRED 0.5~1 mg·kg-1·d -1+AZA 1~2 mg·kg-1·d -1或MMF 1.5~2 g/d治疗,两组间PRED逐渐减量相同,经过倾向匹配评分和调整影响治疗反应与结果的因素后,64例患者被纳入研究。随访结束时,MMF组总体疗效显著高于AZA组,AZA组更易因不耐受停药。一项荟萃分析[15]显示,与标准治疗相比,PRED联合MMF作为一线治疗,AIH患者的生化缓解率较高,无反应率较低。
Roberts等[16]对105例患者使用MMF作为二线治疗,60%的患者12周后达到生化缓解,对标准治疗无反应和不耐受之间的治疗反应相似(57% vs 62%);与无肝硬化患者相比,肝硬化患者的缓解率较低(47% vs 66%),10例(9.2%)患者因不良事件停止治疗。一项荟萃分析[17]表明MMF的缓解率为58%,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4%,停药率为8%。
总体来说,MMF作为二线治疗AIH的效果较高,耐受性良好,因副作用导致的停药率较低,但对肝硬化患者的有效率较低。MMF联合类固醇也可能作为有效的一线替代治疗方法,但仍需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MMF最常见的副作用为胃肠道症状(恶心、呕吐、腹泻),细胞减少,脱发,皮疹,头痛[17]。
AZA进入体内被还原为6-巯基嘌呤(6-mercaptopurine,6-MP)后有三条代谢途径:(1)通过黄嘌呤氧化酶转化为非活性产物6-硫尿酸;(2)通过硫嘌呤甲基转移酶(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ase,TPMT)甲基化后转化为6-甲基巯基嘌呤(6-methylmercaptopurine,6-MMP);(3)通过次黄嘌呤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转化为硫基次黄嘌呤核苷单磷酸,硫基次黄嘌呤核苷单磷酸在肌苷单磷酸脱氢酶和鸟嘌呤单磷酸合成酶的作用下转化成硫基鸟嘌呤单磷酸,最终硫基鸟嘌呤单磷酸可转化为6-硫基(脱氧)鸟嘌呤三磷酸[6-thio(deoxy)guanine triphosphate,6-T(d)GTP]被错配整合到RNA/DNA中,抑制核苷酸和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抑制淋巴细胞的增殖[18]。TPMT为AZA代谢的关键限速酶,TPMT低活性可使6-硫代鸟嘌呤(6-thioguanine,6-TG)生成增加而产生更大的疗效,但骨髓抑制的副作用也增加[18]。编码TPMT的基因具有高度多态性,至少有10个突变等位基因与低酶活性相关,TPMT*3A和TPMT*3B最常见,但与基因分型相比,表型分析避免了种族变异和不完全外显的问题,可以识别TPMT水平低和药物不耐受的个体,具有更好的临床应用价值[19]。
别嘌呤醇的代谢物是TPMT的一种竞争性抑制剂,可将6-MP代谢转向6-TG[18]。别嘌呤醇已成功地用于因代谢改变而对AZA耐药或不耐受的患者[20-21]。别嘌呤醇应在监测药物代谢物显示6-MMP升高、6-TG低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进行联合治疗,同时AZA的剂量应降低到基线的25%~33%,以避免过高的6-TG继发全血细胞减少,这有助于通过识别不依从性患者和6-MMP代谢优先的患者,来指导进一步的治疗[18]。
有回顾性研究[22-23]评估了6-MP对主要因胃肠道症状导致的AZA不耐受患者的影响。Hübener等[22]研究显示15/20例(75%)患者对6-MP治疗有反应,8例完全缓解,7例部分缓解,2例对AZA治疗反应不足的患者对6-MP也无反应。另一项研究[23]对17例AZA不耐受患者随访1年,11/12的患者实现了生化缓解,只有2例患者因不良事件停止治疗。这表明6-MP似乎是一种有效和耐受性良好的二线治疗,但对AZA反应不足的患者可能无效。
AZA代谢过程中生成的多种代谢产物可导致相应的副作用,而6-TG代谢简单,在炎症性肠病中,这种药物已被证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24]。有研究[24]对AZA或MP不耐受的52例AIH患者接受6-TG治疗的记录进行回顾性评估,41例(79%)患者耐受6-TG, 4例(8%)发生耐受不良反应,7例(13%)发生不耐受不良反应;3例患者用6-TG作为一线维持治疗,其中2例在治疗6个月后实现了完全生化缓解;随访18个月,没有发生严重的不良事件。一项研究[25]描述了6-TG治疗17例既往AZA失败的AIH患者的结果,16例(94%)患者在3个月内转氨酶恢复正常,其中11例(64%)得到持续的生物学反应,4例(23%)复发,2例因不良事件(干眼综合征和持续性贫血)停止治疗。8例患者在中位治疗35个月(范围为20~52个月)后进行了肝活检,1例表现为结节性再生增生,但其在治疗前就有一些血管改变。
总之,6-TG可以作为AZA不耐受患者的一个二线治疗选择,但相关数据仍然很少,考虑到其导致的结节性再生增生和肝窦阻塞综合征,使用时应谨慎。
CNI如环孢素A(cyclosporine A,CsA)和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通过抑制淋巴细胞增殖干扰T淋巴细胞介导的反应[1]。
关于CsA抢救治疗成人AIH的数据有限,只在小型回顾性研究[26-27]中报道,虽然研究结果表明有较好的有效性,但数据的质量和数量不足。在儿童方面,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28]对50例儿童使用标准治疗和CsA作为一线治疗,结果表明CsA在诱导儿童AIH的疗效与标准治疗相当,尽管标准治疗组的缓解时间较早。另一项研究[29]对20例儿童患者用CsA作为一线或二线治疗进行了长期随访,治疗的中位数为6.3年,15例75%完全缓解,2例治疗反应不完全,3例肝移植,副作用轻微且短暂。一项对儿童AIH二线治疗的荟萃分析[30]表明,在难治性AIH患儿中,环孢素在6个月的有效率最高,然而,它也有最高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上述研究表明服用环孢素可以安全有效地用于一线或二线治疗,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支持,其副作用包括多毛症、牙龈增生和一过性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一项研究[31]评估了TAC作为AIH患者二线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果18/23例(78%)患者有效,只有1例患者在第3个月因严重的副作用而停用。一项荟萃分析[32]评估了TAC和MMF的疗效及安全性,TAC和MMF的总生化缓解率分别为68.9%、59.6%,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分别为25.5%、24.1%,病死率估计分别为11.5%、9.01%;对标准治疗不耐受的患者,TAC和MMF的生化缓解率分别为56.6%、73.5%,无应答者分别为59.1%、40.8%,表明对于标准治疗不应答的AIH患者,TAC可能优于MMF。
这些数据表明TAC可作为二线治疗,尤其是在对MMF反应欠佳的患者中,并对难治性AIH有效。TAC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神经毒性和胃肠道症状,而糖尿病、肾毒性、瘙痒和脱发也可能发生[32]。
目前AASLD和EASL发布的指南都推荐甲氨蝶呤作为二线替代治疗,但支持的证据较少。一项研究[33]显示11例AIH患者服用甲氨蝶呤,中位剂量每周10 mg,6例(54.5%)在36个月内对甲氨蝶呤产生了完全的生化反应,5例(45.5%)在12个月内停用甲氨蝶呤。甲氨蝶呤价格低廉,容易获得,但其本身具有肝毒性,多达20%的患者在12个月内出现肝酶异常,3~4年至少1次肝功能异常的累积发生率接近50%[33]。

对于一、二线治疗无应答的AIH患者,应重新评估原诊断的准确性和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三线治疗药物包括生物制剂、雷帕霉素哺乳动物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抑制剂等。
英夫利昔单抗是一种TNFα抑制剂,广泛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病和银屑病性关节炎等,目前研究[34]发现,TNFα在肝损伤中发挥作用,通过阻断其作用,可以诱导AIH病情缓解。一项小型研究[35]表明,60%接受英夫利昔单抗治疗的难治性AIH患者病情缓解,但7例出现感染并发症,3例因副作用停止治疗。但在一些研究中也注意到,当这些药物用于治疗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时,它们本身可能导致AIH[34]。因此,当使用抗TNFα抑制剂治疗AIH时要谨慎。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针对B淋巴细胞表面受体CD20的单克隆抗体。一项对22例难治性的AIH患者的研究[36]显示,使用两剂利妥昔单抗后随访24个月,转氨酶改善,类固醇需求减少,复发率降低,只有2例患者由于安全问题中断了治疗。总之,在一些难治性AIH患者中,利妥昔单抗表现出了良好疗效,但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如B淋巴细胞减少、感染等,其安全性必须谨慎评估。
Arvaniti等[37]研究B淋巴细胞激活因子抑制剂贝利木单抗作为2例患者的第三线附加治疗方案,2例患者均获得完全缓解,并在接受低剂量皮质类固醇治疗时持续缓解,未观察到不良事件。这表明,贝利木单抗有希望作为难治性AIH患者的一个选择。
此外,关于伊那鲁单抗、JKB-122、阿巴西普等生物制剂治疗AIH的试验正在进行中。
mTOR抑制剂如西罗莫司、依维莫司,可以减少淋巴细胞的增殖,目前尝试用于AIH的治疗。Chatrath等[38]描述了西罗莫司在5例难治性AIH中的疗效,4例患者转氨酶水平持续下降50%以上,2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所有患者对类固醇的需求均显著减少,副作用是高脂血症和感染。7例难治性AIH患者使用依维莫司治疗,3例患者在治疗1年后持续缓解,副作用为肌痛和轻微细菌感染,未导致停药[39]。鉴于现有的数据非常少,mTOR抑制剂在AIH治疗中的作用仍有待探索。

IL-2对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的发育、克隆扩增和存活至关重要,IL-2与Treg上的三聚体受体结合使其免疫抑制活性增强,释放抗炎因子IL-10;IL-2还上调IL-4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促炎细胞因子IFNγ的分泌,AIH患者的血清IL-2水平较低,Treg对IL-2的反应降低[40]。一项小型试验[41]报告了2例难治性AIH患者使用IL-2 (100万IU)皮下注射,每月连续5 d,为期6个月,只有1例患者治疗结束时转氨酶和IgG水平均降至正常范围,但2例患者的循环Treg比例显著增加,证明了使用低剂量IL-2治疗难治性AIH的可行性。
Tregs于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并在90年代中期得到证实,十多年来,一种采用体外产生的CD4+CD25+Foxp3+Tregs过继转移的细胞疗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42]。活体肝移植后过继转移Treg可使部分患者在移植后3年内摆脱免疫抑制[42]。2016年南京医科大学开始了旨在评估儿童和成人单次输注CD4+CD25+CD127-Treg后的安全性、生化和免疫缓解,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以Treg为基础的治疗的一个主要挑战是产生大量抗原特异性Treg,几种基因操纵的方法已被提出[1]:一种是体外修饰CD4+T淋巴细胞来表达FOXP3,FOXP3是Treg表型的转录因子决定因素;另一种是将特异性T淋巴细胞受体基因转移到Treg的多克隆池中,从而产生对抗原表位的特异性;此外还可通过基因工程特异性识别和消除表达自身反应性抗原受体的致病性B淋巴细胞,同时保持其余的B淋巴细胞。以上方法可在未来尝试用于AIH的治疗。
PIF是一种由存活胚胎分泌的,可促进母体免疫耐受的多肽[43]。一项Ⅰ期临床试验[43]证明了PIF的安全性、耐受性及药代动力学,18例患者被分为三个剂量组(0.1、0.5、1.0 mg/kg),均成功完成试验,没有显著的临床不良事件,所有剂量的耐受性良好,其缺点是半衰期很短(90 min),这意味着需要频繁的皮下注射。
在一项AIH小鼠模型实验[44]中发现, KD可通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来减少代谢相关的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通路和炎症相关的Janus激酶2-信号转导子与转录激活子3通路之间的联系,这诱导了树突状细胞的耐受和代谢抑制,从而中断了树突状细胞和CD8+T淋巴细胞在AIH中的相互作用,显著降低淋巴细胞浸润和促炎细胞因子诱导的肝组织病理学损伤,但不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KD可能是治疗AIH的一种具有潜在疗效的新药物。
一项研究[45]评估了PDE选择性抑制剂在刀豆蛋白-A诱导的AIH小鼠模型中的作用,PDE4可最大程度抑制TNFα和IL-17产生,改善疾病结局,PDE3和PDE7也有这种效应。这可能是AIH的一个有希望的替代治疗策略。

AIH的病因复杂,大多数患者对标准治疗反应良好,但对标准治疗不耐受或无反应患者的治疗选择仍然是一个难题。布地奈德可以被认为是轻度AIH的一线选择,MMF是应用最广泛的二线选择,但反应率、致畸性和耐受性可能是一个问题,支持其他治疗的可靠数据有限。随着对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新型的治疗方法正在开发。对AIH患者应个体化选择最优治疗方案来延缓疾病进展,提高有效率,减少副作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