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
密码过期或已经不安全,请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壹生身份认证协议书
同意
拒绝

同意
拒绝

同意
不同意并跳过





5月19日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该疾病日由欧洲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协会(EFCCA) 组织以及来自五大洲超过50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共同发起,旨在提高公众对于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这种不可治愈的终身疾病的认识和了解。今年世界炎症性肠病日的主题是"IBD没有年龄界限",提出继续关注老年炎症性肠病人群。《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邀请上海瑞金医院消化内科顾于蓓副主任医师为大家详细解析炎症性肠病发病原因,从遗传、感染、免疫、环境和生活饮食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旨在让广大读者深入了解IBD,并更加关注IBD患者的身心健康。

现任亚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AOCC)流行病学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消化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青年学者俱乐部秘书
中华医学会消化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消化内镜俱乐部委员
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第六届胃肠病与营养协作组委员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消化内科 顾于蓓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一类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临床医生最早在北美和北欧的白种人中认识到该疾病,此后在东欧和西欧地区亦陆续发现IBD患者。近几十年来,IBD盛行之风又转向亚洲,尤以东亚各国为甚。从亚洲国家统计资料发现,UC和CD发病率均呈逐年递增,并且UC增幅更快更明显。这一发病现象与半个世纪前的欧美国家发病相似,提示了亚洲各国IBD发病与社会工业化,生活习惯西方化有关[1]。因而推测IBD的发病机制复杂,可能由遗传、感染、免疫、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形成。
CD的发现者Crohn本人早年就已发现CD发病有家族聚集性倾向。CD患者一级亲属患病率为13%-42%,UC为7%-17%。之后,人们又发现同卵双生子同患CD或UC的一致性高达50%和18%,而异卵双生子则分别为10%和4%[2],这一现象成为遗传因素与IBD相关的最好证据。Halfvarson J等甚至发现同卵双生的CD患者在临床表现、病变部位、预后情况等各方面都比较相似[3]。
上世纪90年代起学术界兴起了基因连锁分析的热潮;2001年,首个易感基因NOD2问世。NOD2是定位在16号染色体上的CD易感基因。欧美等国发现约40%CD患者存在NOD2突变。NOD2的问世为之后浩大的易感基因筛选工程拉开了帷幕。值得一提的是,遗传因素在各地区的IBD发病中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欧美国家IBD遗传现象较为普遍,亚洲中以西亚较东亚普遍。NOD2在我国以及临近的日本和韩国均未被报道。这提示遗传机制在地域分布上存在差异,东亚地区可能有较为独特的发病机制。
肠道是人体中微生物最密集的器官。由于IBD临床表现以肠道症状为主,所以人们猜测肠道微生物可能参与IBD发病。临床医生发现IBD患者使用抗生素或要素饮食(减少粪便对肠道刺激)治疗后能改善疾病;病理医生发现肠道病灶处组织对微生物杀伤力下降;科研学者在动物模型中发现肠道在无菌情况下不会发生IBD,因而提出了“无菌就无病”的概念。以上种种迹象均表明,IBD和肠道微生物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4]。
一开始,人们的思维锁定在“某一种特定微生物”感染肠道后触发IBD。在这种思维作用下,不少微生物曾列入候选榜单:例如副结核分枝杆菌、大肠埃希菌、李斯特菌、衣原体、酵母菌、艰难梭菌、麻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腮腺炎病毒等。目前,其中一部分微生物已被证实在IBD患者和正常人肠道内含量无差别;一部分微生物被认为可能在IBD患者肠道内含量增加,但并未得到普遍认同;还有一部分微生物如艰难梭菌、巨细胞病毒已被证实在患者肠道内含量增加,并可能是导致患者活动期病情加重,缓解期病情复发的原因。但大部分学者目前认为艰难梭菌和巨细胞病毒阳性只是IBD患者肠道防御能力下降后产生的临床效应,即二重感染,而并非IBD病因[5]。
之后一系列实验证实:IBD患者粪便和肠道中乳酸杆菌减少,并且活动期较静止期更为明显[6]。人们将焦点渐渐转向“肠道菌群失衡”。根据“菌群失衡”的理论,临床医生开始为患者补充肠道益生菌,并发现肠道益生菌的摄入能有效改善症状。这一事实也有力地证实了菌群失衡在IBD发病中起到了作用。但是,为什么患者肠道内出现菌群失衡现象仍无法解释。学者们推测这可能与多因素相关,如患者的遗传背景,肠道微生物组成、摄食、迁徙,肠道内pH值、温度、氧化还原情况等。
IBD是一种肠道免疫异常活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经典理论认为:在适应性免疫异常中,CD是以Th1细胞介导,体内以IL-4、IL-13等细胞因子升高为主的自身免疫病,而UC则由Th2细胞介导,主要表现为IFN-τ等细胞因子升高。此后,Th17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这两个T细胞亚群在IBD发病中广受关注。在IBD发病中除了上述的Th1、Th2、Th17、调节性T细胞这4种T细胞亚群外,其他免疫细胞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树枝状细胞、巨噬细胞可通过分泌TNFα加重疾病;而记忆性T细胞则可能是IBD持久不愈的原因之一。
随着研究的进展,固有免疫异常也日益受到重视。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异常不同的是:固有免疫在IBD发病中其作用是受到抑制的,而并非异常活化的。益生菌应用于IBD治疗有效这一事实证明了固有免疫在IBD治疗中是需要受到刺激的。肠道免疫异常是基于有遗传易感背景的人群受到肠道细菌感染而产生的。因而免疫因素在IBD发病中与遗传因素和感染因素息息相关。
IBD发病与社会工业化,人们生活习惯西方化密切相关。因而环境因素可能对IBD发病起促进或保护作用。早在20世纪已有学者提出“卫生学假说”,卫生学假说是指当儿童在过分卫生的环境下发育成长,环境因素可能对儿童免疫系统的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日后发生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包括IBD。卫生学假说中提出的危险因素包括:婴幼儿期注射麻疹疫苗或卡介苗、干净的水质、热水龙头使用、咀嚼口香糖、使用冰箱、家庭规模小、居住在城市、单独使用卧房等。而感染肠道寄生虫、幽门螺杆菌则可能是IBD发病的保护因素[7]。
吸烟对IBD发病有很大影响。吸烟能下调患者体内Th2作用,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吸烟是CD的危险因素,而对UC则起保护作用。约45%~55%CD患者吸烟,研究显示吸烟者较不吸烟者更容易发展为CD,并且吸烟会增加CD患者的合并症、复发率、手术率以及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用量,然而吸烟患者一旦戒烟后危险因素则可去除。
饮食被认为是与IBD发病最相关的因素。在西化的饮食结构中,位于能量金字塔顶端的食物摄入过多,如高糖、高动物脂肪、高蛋白饮食;而位于能量金字塔底端的食物却摄入减少,如高纤维饮食,碳水化合物。诸多学者指出,IBD患者摄入肉类、乳制品、糖分较多,而食用大米较少[8]。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肉类(尤其是红肉)、乳制品、酒精、精制糖是IBD危险因素,而鱼油(ώ-脂肪酸)、粗纤维食物则为IBD发病的保护因素[6]。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某项致病食物,但相信针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IBD发病。
其他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包括服用NSAID类药物、避孕药物、儿童期使用过多抗生素、精神压力大等;保护因素有母乳喂养等。
IBD的发病率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存在明显变化。尽管IBD确切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知晓,但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未知机制的探索。目前认为,IBD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病机制是具有遗传背景的易感者受到肠道细菌的感染,引发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疾病。在这一过程中,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因素均可加重或减轻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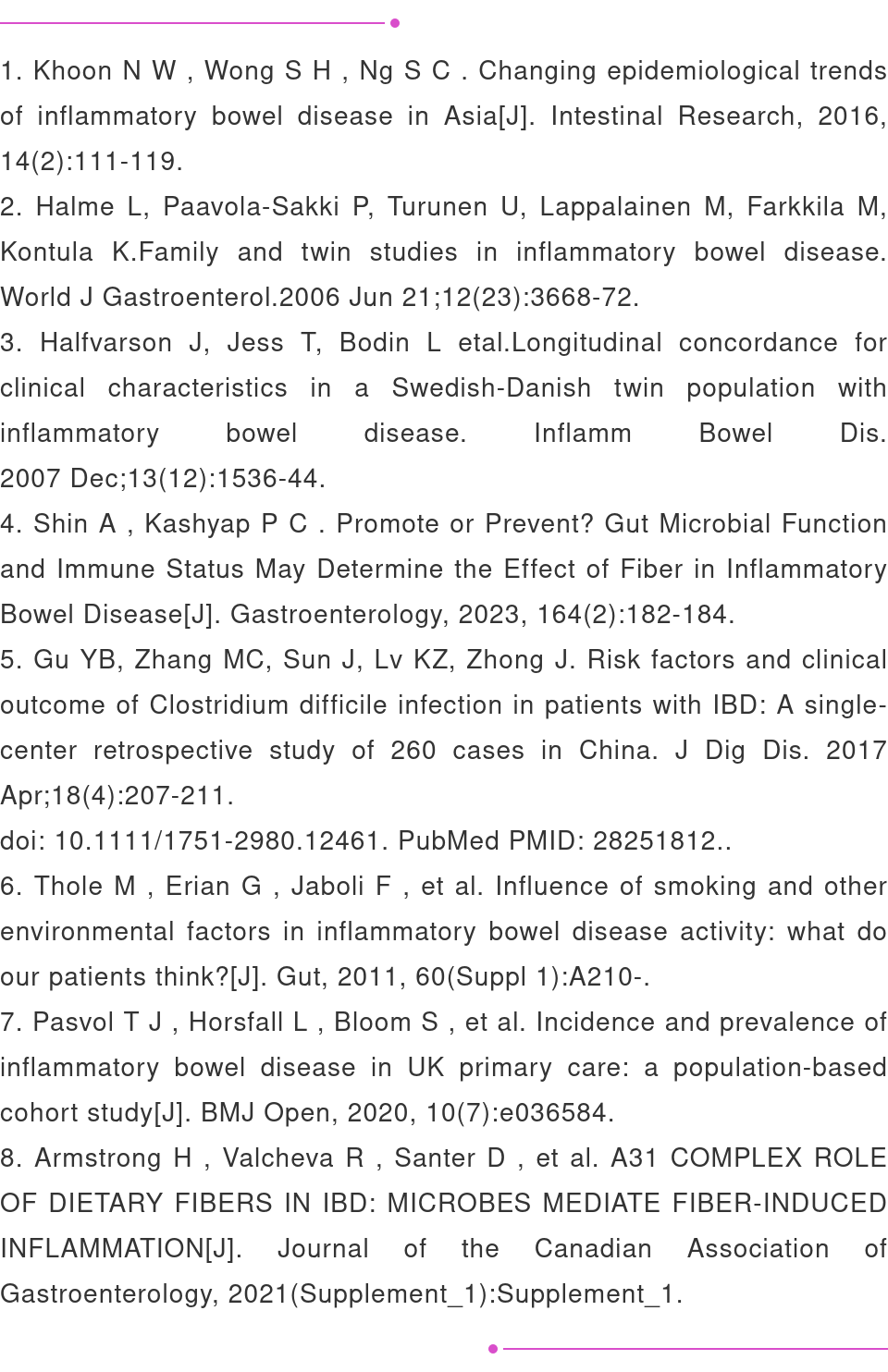
(本文版权属于中国医学论坛报社,转载需授权)
查看更多